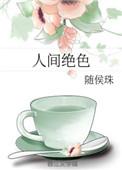第五章 中国人为什么生气 (2)(12 / 24)
么来的?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,不知去哪儿接你呢!”
“坐公共汽车来的,路上淋湿的。”
“干吗不坐出租汽车?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!”
“能省就省点儿吧,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……”
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——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,见小说家们的手稿,是在拥挤不堪的、光线不足的、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,被编排出版,就觉得寒心。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,可谓同病相怜。
“是啊是啊……”比我还瘦的老杜,搓着他的双手,做豪迈状地笑着,感激地说,“你能这么体恤我们,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!不过嘛,编辑部再穷,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……你有没有衣服换啊?”
我说有。他说换上换上,湿漉漉的,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……
这时我才发现,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——细想了想,大概是丢在《羊城晚报》的传达室了……
老杜很有些急——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,快一同去找找……
雨仍未停。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,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。我看得出,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,只好服从。结果是他没拦到。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。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。我一来,他会也开不成,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,便有几分拘谨。其实,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——书卷气十足,热情,真挚,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。
《羊城晚报》招待所,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,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——一张单人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竟还有一张沙发。无窗。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。房租很便宜——十五元。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,十五元住单间,条件算相当不错了。何况还有电视机。
各自落座,说了几句话,到中午了,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。我拗他不过,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。
吃饭间,老杜问:“房间大小,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?”
我说:“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。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。”
第二天起,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,写《冰坝》。刚从大学毕业时,我一天可写一万字。而现在,每天写四千字,已是从早写到晚,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。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。不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
“坐公共汽车来的,路上淋湿的。”
“干吗不坐出租汽车?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!”
“能省就省点儿吧,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……”
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——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,见小说家们的手稿,是在拥挤不堪的、光线不足的、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,被编排出版,就觉得寒心。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,可谓同病相怜。
“是啊是啊……”比我还瘦的老杜,搓着他的双手,做豪迈状地笑着,感激地说,“你能这么体恤我们,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!不过嘛,编辑部再穷,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……你有没有衣服换啊?”
我说有。他说换上换上,湿漉漉的,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……
这时我才发现,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——细想了想,大概是丢在《羊城晚报》的传达室了……
老杜很有些急——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,快一同去找找……
雨仍未停。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,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。我看得出,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,只好服从。结果是他没拦到。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。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。我一来,他会也开不成,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,便有几分拘谨。其实,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——书卷气十足,热情,真挚,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。
《羊城晚报》招待所,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,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——一张单人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竟还有一张沙发。无窗。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。房租很便宜——十五元。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,十五元住单间,条件算相当不错了。何况还有电视机。
各自落座,说了几句话,到中午了,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。我拗他不过,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。
吃饭间,老杜问:“房间大小,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?”
我说:“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。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。”
第二天起,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,写《冰坝》。刚从大学毕业时,我一天可写一万字。而现在,每天写四千字,已是从早写到晚,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。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。不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
相关小说
- 地球上线
- 这是一本关于结婚以后的故事,婚姻需要温馨点,可爱点,幸福点,还要那个嘿咻之事也理直气壮点……<BR>本书女主人公婚后的幸福生活似乎有些不同寻常,老公的爱是变态的爱,为了让妻子幸福快乐,他把她逐步引向yin乱,不过她从中得到了很幸福很快乐的生活,自然老公也...
- 06-22
- 致命偏宠
- 【已签出版】 黎家团宠的小千金黎俏,被退婚了。 黎家人揭竿而起,全城讨伐,誓要对方好看。 * 后来,黎俏偶遇退婚男的大哥。 有人说:他是南洋最神秘的男人,姓商,名郁,字少衍; 也有人说:他傲睨万物,且偏执成性,是南洋地下霸主,不可招惹。 绵绵细雨中...
- 06-22
- 人间绝色
- 文案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。 你是我的,人间绝色。 内容标签:都市情缘 破镜重圆 天作之合 平步青云 主角:颜艺,顾嘉瑞 ┃ 配角:若干 ┃ 其它:……
- 05-09
- 最强医圣
- 《最强医圣》是左耳思念精心创作的其他类型,全本小说网实时更新最强医圣最新章节并且提供无弹窗阅读,书友所发表的最强医圣评论,并不代表全本小说网赞同或者支持最强医圣读者的观点。 带着一身通天本领强势回归。会治病、会算命、会炼药、会摆阵、会炼符……“这个...
- 07-04
- 默读
- 童年,成长经历,家庭背景,社会关系,创伤…… 我们不断追溯与求索犯罪者的动机,探寻其中最幽微的喜怒哀乐,不是为了设身处地地同情、乃至于原谅他们,不是为了给罪行以开脱的理由,不是为了跪服于所谓人性的复杂,不是为了反思社会矛盾,更不是为了把自己也异化成...
- 05-28
- 十三幺
- 【文案】 陈许泽有个小名,听说是出生前,陈奶奶和周妈妈在同一个牌桌上先后摸到了十三幺, 于是周窈和陈许泽,她占“幺”字,他占“十三”。 得知他们曾经有过口头上的娃娃亲,损友差点没笑死。 陈许泽沉闷冷漠,桀骜自我,对谁都不屑一顾。 ...
- 07-18